
編者按:2022年7月6日,由三峽川劇藝術(shù)研究傳承中心(重慶市三峽川劇團(tuán))創(chuàng)排的本土原創(chuàng)現(xiàn)代川劇《峽江月》登上第五屆川劇節(jié)舞臺。該劇是重慶市近年來新創(chuàng)川劇的代表劇目之一;是“萬州戲劇現(xiàn)象”的又一亮點(diǎn);是聞名遐邇的“下川東”川劇藝術(shù)傳統(tǒng)的再度轉(zhuǎn)身與亮相。重慶市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邀請文化評論者和部分觀眾參與本劇的觀評活動,他們將從劇目緣起、文化背景、藝術(shù)特色、呈現(xiàn)情況等方面,對本劇進(jìn)行介紹和討論。
最是皎潔峽江月,清輝滿地人間情
——現(xiàn)代川劇《峽江月》觀后感
重慶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 張志全
一輪明月,映照出巍峨山峰、滾滾浪濤。嗩吶聲中,一曲山歌飄然而至:“峽山高來江水平,明月有光人有情。妹心似月天上掛,不知哥心可有人……”重慶三峽川劇傳承中心編演的現(xiàn)代川劇《峽江月》甫一開場,即先聲奪人,將全場觀眾帶到了唱響竹枝情緣的峽江風(fēng)情之中。

不錯,《峽江月》描述的是峽江兒女的情愛故事。貫穿于全劇的是身為寡婦的望江客棧老板江小月,在二十余年間先后與兩個男人(水老大、表兄劉望)的絕世之戀。然而,《峽江月》又不只是描述普通的男女之情。編劇將故事的背景放在了近現(xiàn)代史上最波瀾壯闊的民族獨(dú)立與解放運(yùn)動時期,從而賦予了男女情愛以厚重的歷史感與滄桑感。由此,背景已不再是背景,背景轉(zhuǎn)化為故事的骨架,主導(dǎo)著戲劇的敘事與主題的顯現(xiàn)。這樣的巧妙構(gòu)思,不禁令人想起歷來為曲家所稱道的清代傳奇《桃花扇》之構(gòu)局:“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峽江月》的兒女之情,不過是故事演繹的表層邏輯。只是,編劇已不再屬意于“興亡之感”這一歷史局限,而是站在民族覺醒的高度,抒寫中華兒女在民族存亡之際的使命擔(dān)當(dāng)與不朽抗?fàn)帯?/p>
如果說《桃花扇》是以“扇”作為“穿云入霧”之珠,那么,《峽江月》則是以“月”作為總攬全劇之魂。“月”首先是自然物象。《水經(jīng)注?三峽》云:“(三峽)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獨(dú)特的自然風(fēng)貌,使峽江月的清輝,顯得彌足珍貴。劇本名之曰“峽江月”,是編劇有意將“峽江之月”的物象特征加以抽象,并以此引入戲劇的敘事結(jié)構(gòu)之中。“最是皎潔峽江月,清輝滿地人間情”,于是,“月”化身為飽含深情的“意象”之月。“月”是愛情的寄寓之地,也是情感的升華之境。作為峽江之月的人格化構(gòu)型,劇中的女主角江小月,既是水老大的心中之月,也是其表兄劉望畢生守護(hù)的“生命之月”。江小月雖然遭逢亂世,早年守寡,但她的勤勞善良、深明大義、歷經(jīng)劫難而無所畏懼,一如月之清輝惠澤萬川。她承受著常人所無法想象的痛苦:“九五慘案”中丈夫的慘死、抗戰(zhàn)之中戀人“水老大”的犧牲與兒子的以身殉國、國共內(nèi)戰(zhàn)之中摯愛她一生的男人離世。樁樁件件,非但未能打垮這個平凡女子活下去的勇氣,反而練就了她堅(jiān)韌而不屈的意志。她的覺醒是自發(fā)的,也是義無反顧的!表面看來,《峽江月》只是濃墨重彩地刻畫了“一個”峽江女子的“俠骨柔情”與“大義凜然”,然而,編劇有意將“弱女子”與“大時代”相對應(yīng),以此形成張力敘事結(jié)構(gòu),無形中拓展和深化了戲劇之主題。在這樣的大時代中,江小月顯然不只是個體的存在,江小月變成“江小月們”,成為一個群體的象征。他們是平凡的,生前不曾名世,身后亦不曾留名。他們又是最不能被遺忘的,他們在不平凡的年代里,以質(zhì)樸的行為,成就了一片清明,賦寫了不屈的生命之歌。

圍繞以上戲劇結(jié)構(gòu),《峽江月》的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致力于舞臺設(shè)計(jì)上的探索。作為新編現(xiàn)代川劇,舞臺道具自然已非傳統(tǒng)的一桌二椅可比,現(xiàn)代技術(shù)手段為戲曲舞臺的多元審美提供了可能。就全劇來看,舞臺布設(shè)在一定程度上顯現(xiàn)出實(shí)景化傾向,比如望江客棧的布置:方桌、條凳、茶客、伙計(jì)、被炮火摧斷的黃葛樹、青石香爐,以及客棧壁上的標(biāo)語“國家有難,匹夫有責(zé)”;比如峽江浪濤的背景、木船與碼頭,以及日機(jī)轟炸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寫實(shí)與半寫實(shí)的畫面和聲響,帶給了觀眾沉浸式的視聽震撼。當(dāng)然,如果只是一味追求實(shí)景化效應(yīng),必然背離戲曲舞臺的美學(xué)原則,為此,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極力營建寫意化的審美空間。既然“月”是劇作的核心意象,如何將“劇中之月”轉(zhuǎn)化為“舞臺之月”自然成為了舞臺設(shè)計(jì)的重中之重。在現(xiàn)代技術(shù)輔助之下,伴隨劇情的發(fā)展,舞臺之月時而圓如銀盤,時而缺如彎鉤,形成天上月、人間月與心中月的相互映襯,實(shí)景之月由此轉(zhuǎn)化為虛擬的符號,呼應(yīng)著故事的演進(jìn)與情感的律動。在舞臺演繹之中,“月形”的舞臺設(shè)計(jì)還承擔(dān)著表演場景界分、表演區(qū)劃定等功能。比如,第一場中水老大駕乘木船駛進(jìn)碼頭,嗩吶聲起,客棧內(nèi)的茶客與伙計(jì)皆循聲望向窗外。此時,本為背景的“月形”幻化為客棧臨江之窗口,與客棧內(nèi)的場景相對應(yīng),很自然地賦予舞臺畫面以縱深感。這一前后景的電影化構(gòu)圖,為水老大這個核心角色的出場,鋪設(shè)了足夠的排場。“月形”之內(nèi)(后),是舞臺展演中特定的表演區(qū),戲劇的開場與結(jié)尾、江小月與水老大的“碼頭之會”、水老大與船工們“炮火連天闖峽江”、江小月與劉望的“白綢之舞”等等,都放在“月形”表演區(qū)之中。這一表演區(qū)的設(shè)定,使戲劇舞臺自然形成前后表演區(qū)與前后景的界分。舞臺表演中,兩個表演區(qū)或連成一體,或相互分離,各自承擔(dān)著相應(yīng)的表演功能。其中,“月形”之中的表演區(qū),側(cè)重于載歌載舞的動作表演,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遠(yuǎn)虛近實(shí)”的舞臺效果。可以說,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深諳“月”意象在中國文化中的深層意蘊(yùn),以“月”之生動氣韻,為戲劇的詩性表達(dá)賦形。故此,所謂“逼真”的“舞臺之月”,化身為層累千年的“人文之月”,本質(zhì)上成就了《峽江月》成為“詩劇”之可能。
《峽江月》的舞臺布置,為虛實(shí)相生的藝術(shù)表達(dá)奠定了基礎(chǔ)。新編現(xiàn)代戲在很大程度上保留戲曲程式性與古典韻味,歷來是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因而,自上世紀(jì)80年代初,戲曲界針對現(xiàn)代戲創(chuàng)作中的“話劇加唱”傾向,提出了“戲曲化”概念。“戲曲化”作為對“戲曲”舞臺表演的要求,嚴(yán)格地說有些不倫不類。但是,面對當(dāng)下戲曲的困境,“戲曲化”概念對于糾偏戲曲表演異化,呼吁回歸表演傳統(tǒng)等方面的作用,已然在學(xué)界達(dá)成共識。“戲曲化”就是要規(guī)避舞臺表演的過度寫實(shí)化、生活化傾向,力圖在“虛”與“實(shí)”中尋找平衡點(diǎn)。“戲曲化”更多是對表演程式與聲腔的約定,要求以現(xiàn)代劇場的表現(xiàn)手段,烘托“戲曲表演的單純、精粹、絕美,進(jìn)而擴(kuò)展自然人身體與聲音的表現(xiàn)力與感染力”(羅懷臻語),讓戲曲表演重新回到虛擬寫意的傳統(tǒng)美學(xué)表達(dá)中。可見,“戲曲化”的回歸,不是斤斤于古法,也不是毫無根據(jù)的創(chuàng)新,而是在遵循戲曲審美精神的前提下,基于傳統(tǒng)戲曲功法的“情境化”“個性化”再造。《峽江月》的舞美,充分吸收并融匯傳統(tǒng)表演程式,使舞臺敘事富于寫意化的韻律美與節(jié)奏感。如江小月與劉望勇闖峽江,尋找逾期未歸的水老大這一場戲:以槳代船,角色隨浪濤起伏而動……觀眾眼前不禁浮現(xiàn)出川劇《秋江》的經(jīng)典畫面;又如,水老大與船工勇闖峽江的一場戲,導(dǎo)演將傳統(tǒng)的戲曲程式與現(xiàn)代舞蹈動作相融合,應(yīng)和著“月形”上寫實(shí)化的“峽江浪濤”畫面和鏗鏘有力的船工號子,編創(chuàng)了兼具程式美與生活化的“船工之舞”。此外,水老大與江小月的碼頭離別、江小月與劉望的“白綢之舞”都在傳達(dá)畫面寫實(shí)感的同時,著力張揚(yáng)戲曲的寫意化美學(xué)。誠然,《峽江月》的“戲曲化”并不徹底,一些地方仍有明顯的“話劇色彩”,但是,在融匯傳統(tǒng)戲曲功法與戲劇情境上,《峽江月》作出了頗有意義的探索。

如果說“戲曲化”是戲曲表演的內(nèi)在要求,“地方性”則是地方劇種的根本屬性。從廣義上講,無論哪一種戲曲樣式,都是地方民俗文化與審美趣味在舞臺藝術(shù)中的集體呈現(xiàn),承載著一方庶民群體的生命精神與生存愿景。方言是各劇種“地方性”最為顯著的特征。在《峽江月》的曲詞中,編劇使用大量生動俏皮的巴渝方言土語,如“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連兒桿拗不過大腿”“癩疙寶想吃天鵝肉”“叫你龜兒都完蛋”等等,有的難免有些粗俗,但從劇中人物的口中道出,顯得并不突兀。方言俗語的運(yùn)用,使劇本一定程度上脫離了文人創(chuàng)作的書卷氣息,具有濃烈的蛤蜊風(fēng)味和民間色彩。地域民俗文化的廣泛運(yùn)用,進(jìn)一步反映了《峽江月》主創(chuàng)團(tuán)隊(duì)向“地方性”回歸的決心。作為傳統(tǒng)社會最為民眾喜聞樂見的舞臺藝術(shù),地方戲的展演浸染著豐富多樣的民間藝術(shù)樣式,可以說傳統(tǒng)社會的地方戲展演,本身就是地方民俗文化的“跨界”匯融。在《峽江月》之中,導(dǎo)演團(tuán)隊(duì)廣泛引入峽江地區(qū)的民俗藝術(shù):戲劇開場中的嗩吶與山歌、貫穿于舞臺始終的竹琴、迎親儀式上的板凳龍、質(zhì)樸歡快的打蓮廂、粗獷鏗鏘的船工號子……洋溢著濃濃的峽江風(fēng)情。而且,以上民間文藝形式并非生硬地拼接在舞臺上,而是力圖植入到故事的肌理之中,用以承擔(dān)舞臺敘事的功能。比如,全劇在山歌聲中開啟,又在山歌聲中落幕,“妹心似月天上掛,不知可心可有人”,“最是皎潔峽江月,清輝滿地人間情”,清新俚俗、情意綿綿的情歌對唱,并非游離于故事之外,而是與整個劇情形成呼應(yīng),是對戲劇人物和故事主題的詩性概括。而第五場中“船工號子”的運(yùn)用,生動形象地賦寫了水老大及船工們“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的豪情,這是刻畫水老大這一角色不可缺少的戲劇情境。
當(dāng)然,《峽江月》從戲劇文本到舞臺表達(dá)上,難免還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比如,在故事節(jié)奏和情感邏輯方面,如何處理好前六場與第七場之后的關(guān)系?如何更好地在現(xiàn)代舞臺上,充分發(fā)揮川劇程式在情感敘事中的魅力?不過,作為一部新編現(xiàn)代川劇,《峽江月》無疑是近年來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我們相信,假以時日,《峽江月》必將取得更大成就,成為新編現(xiàn)代戲的典范之作。
(本文照片由余小武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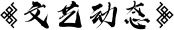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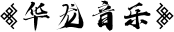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