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董小玉 何艷
“觀看先于言語。兒童先觀看,后辨認,再說話。”約翰·伯格在《觀看之道》開篇的這句話語,猶如雷鳴般振聾發聵,重塑我們對視覺的價值體認。這部誕生于 1972 年的文化巨著,脫胎于 BBC 同名電視系列節目,一經問世便引發全球轟動。其譯本如星子散落,覆蓋數十種語言版圖,不僅穩坐全球藝術院校核心書單,更成為滋養數代學人思想的精神沃土,在藝術批評與文化研究領域樹起不可逾越的豐碑。《觀看之道》的革命性意義,在于它以銳利的智識之劍,劈開 “觀看” 這一日常行為的表象,剖析出背后潛藏的權力網絡與意識形態密碼,成功將大眾從視覺消費的被動受體,鍛造為具備批判自覺的文化解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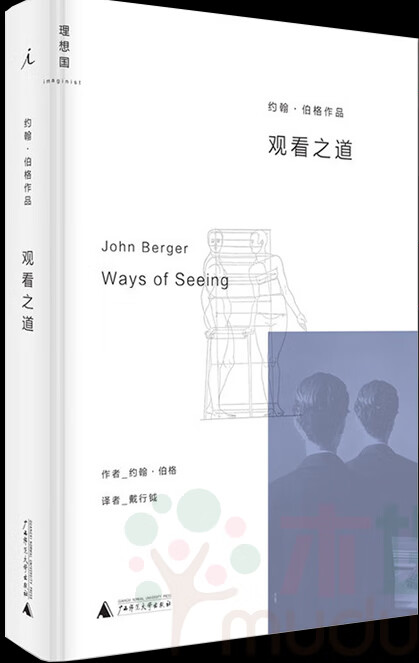
解構視覺神話:觀看是感官與思維的結合
伯格最根本的顛覆在于揭示了觀看行為本身受制于歷史和社會條件這一本質現象。我們習慣于認為“眼見為實”,并將視覺視為最直接、最真實的感知方式。然而伯格卻指出:“我們從不只是看一樣東西;我們總是在看東西與我們之間的關系。”觀看的意義,或許就隱藏在凝視與被凝視之間的關系上。維特根斯坦也認為看似簡單的“看”其實包含復雜的認知活動。
在分析歐洲裸體畫傳統時,伯格展示了男性凝視如何被自然化為普遍的觀看方式。他指出:“男子重行動,女子重外觀。男性觀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男性觀察。”這一簡單的觀察揭示了藝術史中隱藏的性別政治——女性被客體化為被觀看的對象,而男性則占據著觀看主體的位置。伯格的分析不僅適用于古典油畫,也同樣適用于當代廣告圖像。當我們今天瀏覽社交媒體或商業廣告時,這種視覺權力的不對稱分配依然清晰可辨,足以證明伯格的批判視角具有驚人的時代超越性。
更激進的是,伯格祛除了藝術“靈光”的神秘性。在本雅明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指出,藝術作品的權威不僅來自其獨特性,更來自一整套博物館、藝術史、拍賣行等制度所賦予的社會價值。如今,梵高的向日葵被印在咖啡杯上,蒙娜麗莎成為表情包,伯格所預見的正是機械復制時代藝術神圣性的消解過程。這種解構不是價值的貶損,而是將藝術從神壇拉回人間,使其成為人人可以參與討論的公共話題,并具有了社會價值。
視覺的資本邏輯:當觀看成為商品的占有
伯格將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延伸至視覺領域,提出了一個震撼性的觀點:觀看方式反映并強化著財產關系。在歐洲油畫傳統中,肖像畫和風景畫不僅僅是藝術藏品,更是財產清單和所有權聲明。“油畫要歌頌私有財產。它本身就是一份屬于某個人的財產,而且它描繪的也是財產。”這一洞察揭示了藝術形式與社會經濟結構之間的深層聯系。
這種視覺占有在當代社會演變為更加隱蔽的形式。廣告圖像不再直接展示財產,而是創造欲望和缺失感,將觀看轉化為永不滿意的消費循環。伯格尖銳地指出:“廣告關注的是人際關系,而不是物品。它承諾的不是快樂,而是快樂的可能性——在他人眼中顯得快樂的可能性。”這種分析解釋了為何在物質豐富的時代,廣告反而更加無處不在——它不再銷售產品,而是銷售通過他人眼光確認的自我形象。數字時代更將這種邏輯推向極致,社交媒體使每道目光都蘊含經濟價值,“點贊”與“觀看量”成為新貨幣,我們同時是觀看的消費者與被看的商品。伯格40年前的洞見,為我們理解當下瘋狂生產與消費圖像時究竟在參與何種關系的再生產,提供了至關重要的鑰匙。
抵抗的視覺:重建觀看的平等對話
伯格積極探索視覺實踐解放的可能性。他推崇那些打破常規觀看方式的藝術實踐,如弗朗西斯·培根扭曲的肖像,或紀錄片攝影師對邊緣群體的呈現。這些實踐的重要性在于它們“不是邀請觀眾占有被描繪者,而是邀請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
伯格對攝影的討論尤其具有啟發性。與油畫不同,攝影本質上具有民主潛力——它不依賴于長期訓練,可以捕捉未被編排的現實,能夠無限復制傳播。伯格認為:“攝影師做出的選擇不是繪畫性質的選擇,而是程序性質的選擇,更像是見證人的選擇而非演員的選擇。”這一特性使攝影可能成為抵抗視覺霸權的工具,盡管它同樣容易被商業和權力收編。
在當代語境下,手機攝影和社交媒體的普及實現了伯格的愿景。普通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圖像生產能力,傳統視覺權威被不斷挑戰。阿拉伯之春中手機拍攝的抗議畫面,黑人運動中流傳的警察暴力視頻,都驗證了伯格式的“抵抗視覺”在數字時代的生命力。然而,這種民主化也伴隨著新的問題——圖像泛濫、真相危機、注意力經濟對人的捕獲。伯格的思考提醒我們,技術本身不具解放性,關鍵在于我們如何使用它,以及我們發展出了怎樣的視覺素養來駕馭它。
“在一個被影像包圍的世界里,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學會觀看。”伯格的這一警示在今天顯得尤為緊迫。《觀看之道》出版近半個世紀后,我們生活在一個視覺刺激前所未有的時代,但我們的觀看能力是否真的進步了?我們是否能夠穿透圖像的表面,理解其背后的多層深意?使“心中之眼”明亮起來。
法國思想家福柯曾說:“重要的不是話語講述的時代,而是講述話語的時代”,這可以是為約翰?伯格《觀看之道》量身定制的注腳。這部誕生于視覺革命前夜的經典,不僅是解剖 1970 年代視覺政治的鋒利手術刀,更鍛造出穿透時空的分析棱鏡 —— 當 AI 繪圖的算法迷霧、深度偽造的數字陷阱,以及虛擬現實的感官繭房重構人類視覺認知時,伯格對觀看機制的批判性解構,正以驚人的預見性洞燭當代視覺困境。這種將 “觀看” 從本能行為升華為反思性實踐的智識突破,本質上是一場關于認知主權的隱秘革命 —— 當我們開始叩問視覺經驗的建構邏輯,實則已悄然改寫著人類與世界對話的底層代碼。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