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董小玉 譚丹
作為第一位獲得諾獎(jiǎng)的亞洲女性,韓國(guó)作家韓江走入大眾視野。諾獎(jiǎng)給她的頒獎(jiǎng)詞寫(xiě)道:“充滿詩(shī)意的散文直面歷史創(chuàng)傷,揭露人類生命的脆弱。”她揭露了當(dāng)代人的精神困境,小說(shuō)《素食者》尤為典型,這本書(shū)在2022年獲得了布克國(guó)際文學(xué)獎(jiǎng),評(píng)獎(jiǎng)主席博伊德·唐金稱贊道“這本凝練、精美而又令人不安的書(shū)將長(zhǎng)久縈繞于人心,甚至潛入讀者的夢(mèng)中。”書(shū)中的女主人公英惠,讓人聯(lián)想到卡夫卡小說(shuō)《變形記》里變成了甲殼蟲(chóng)的主人公格里高爾·薩姆沙。《素食者》中的英惠變成了植物,永久地扎根于地底,不悲不喜、不破不立,植物和動(dòng)物的區(qū)別在于動(dòng)物有著動(dòng)的性質(zhì),而植物則是無(wú)悲無(wú)喜,長(zhǎng)久地靜靜地站在那里,這意味著英惠最終沖破了欲望之軀,擺脫了這個(gè)淫穢的世界,從而讓自己的靈魂獲得新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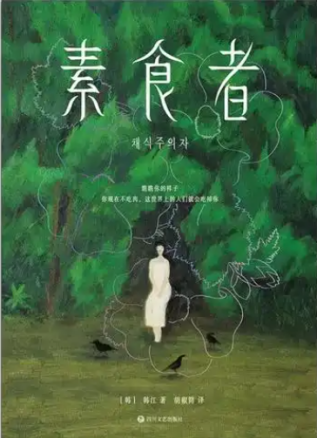
一、拒絕吃肉,隱射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壓抑
第一部“素食者”,經(jīng)歷噩夢(mèng)之后,英惠突然開(kāi)始拒絕吃肉,拒絕為家人準(zhǔn)備葷菜,這是一個(gè)關(guān)于各種各樣臉的夢(mèng),這些臉或許是一個(gè)又一個(gè)受英惠壓迫或是壓迫了她的人,吃與被吃在英惠的夢(mèng)里得到了真實(shí)的體驗(yàn)。薩特說(shuō):“不經(jīng)意間的夢(mèng)境反映了我們內(nèi)心深處的欲望和恐懼”,夢(mèng)是現(xiàn)實(shí)的反映,英惠在日常的生活中得不到任何快樂(lè),幼時(shí)受父親的暴力打壓,長(zhǎng)大結(jié)婚后受到丈夫的冷暴力。
英惠在兒時(shí)曾被一只狗咬傷,然而這只狗卻被車活生生地拖著跑死了,最后這狗肉被他們一家人分而食之,小時(shí)候的英惠只是靜靜地看著這一切發(fā)生,口中念著“我不在乎,我一點(diǎn)都不在乎”。一個(gè)人在撒謊時(shí)才常常會(huì)反復(fù)重申,這反映出英惠內(nèi)心的善良,她的心里十分在乎這一條弱小的生命,但她卻不敢反抗,這只狗在多年后也進(jìn)入到英惠的夢(mèng)中,成為了一張張具象化的臉。
結(jié)婚后,在丈夫眼中,英惠就是最平凡普通的一個(gè)女人——溫順、懂事、事事為他著想,且“經(jīng)濟(jì)實(shí)惠”。丈夫需要的不是一位“妻子”,而是一個(gè)保姆、一個(gè)固定的發(fā)泄對(duì)象。長(zhǎng)期的冷暴力加劇了英惠的精神負(fù)擔(dān),“一望無(wú)際的黑暗,所有的一切黑壓壓地揉成了一團(tuán)”。于是在一天晚上她覺(jué)醒了,決定向世界宣告自己的不滿,從不吃肉開(kāi)始,這個(gè)肉可以看作是一種社會(huì)暴力的象征。人類不吃肉是難以生存的,肉都來(lái)源于動(dòng)物,動(dòng)物和人類一樣是具有靈性的生命,吃肉也是在吃掉我們的同伴,施暴于我們的同伴,所以英惠選擇吃素就是在反抗當(dāng)代社會(huì)的隱形暴力。
生活中,我們都處在英惠這樣的境地里,我們無(wú)法忍受別人異樣的眼光,無(wú)法看清自己的所思所想,對(duì)比之下,英惠則是清醒的,在充滿肉欲的煙火世界里,英惠活成了反抗傳統(tǒng)肉欲與煙火的符號(hào)。
二、選擇出走,深諳人性灰暗的底色
第二部“胎記”,英惠的丈夫無(wú)法忍受妻子的怪異,于是提出了離婚,與其說(shuō)是丈夫提出了離婚,不如說(shuō)是英惠選擇了出走。在他們的婚姻中,丈夫其實(shí)是一個(gè)可有可無(wú)的角色,是英惠撐起了這一段婚姻,一旦英惠選擇了不再維持,這段婚姻也就沒(méi)有了繼續(xù)的必要。這時(shí),一個(gè)集藝術(shù)與瘋狂于一體的男人——姐夫,在英惠的世界中激起了漣漪,如果沒(méi)有這個(gè)人的出現(xiàn),英惠的生活或許真的可以歸于平靜,但正是這樣一個(gè)打著藝術(shù)之名,加劇了英惠的精神疾病,使她對(duì)于人類社會(huì)徹底失望,徹底將自己“樹(shù)化”。
姐夫在英惠的身上畫(huà)出了一朵朵花,青色的胎記仿佛擁有了無(wú)限的生命力,這樣一幅畫(huà)面本應(yīng)是很美的。姐夫在英惠身上畫(huà)了還不夠,還想要這朵花結(jié)出果實(shí),于是有了后來(lái)那“瘋狂”的一夜。這一夜使她“擺脫”了夢(mèng)的困擾,她真正明白了世界惡的源頭——是這個(gè)世界上無(wú)數(shù)的吃人的人。
在“胎記”這一章,英惠從糟糕的婚姻中出走,她的內(nèi)心在不斷地強(qiáng)大,對(duì)這個(gè)世界的看法也在進(jìn)一步完善,這種完善毋寧說(shuō)是一種失望到了極點(diǎn),從而加劇了精神上的疾病。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曾言:“沒(méi)有比賦予疾病以某種意義更具懲罰性的了——被賦予的意義無(wú)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義。”英惠的這種樹(shù)化其實(shí)就是這種充斥著無(wú)數(shù)意義的疾病,但是這也意味著她在不斷地追尋著內(nèi)心的平靜和自由、追尋著人生真正的意義。有讀者在讀完本書(shū)后寫(xiě)道:“《素食者》是極致的暴力與美,也是極致的壓抑與解放。”在看似荒誕的故事背后,其實(shí)折射出的卻是人性的底色:欲望、占有、暴力、拋棄、反叛和解放。
三、擺脫淫穢,把自己變成一棵樹(shù)
第三部“樹(shù)火”,英惠把自己“變成”了一棵樹(shù)。在經(jīng)歷與姐夫的丑聞后,病情加重,父母拋棄,姐夫潛逃,英惠開(kāi)始走向“發(fā)瘋”,她逐漸把自己“變成”一棵樹(shù),成為植物一樣的存在,只需要陽(yáng)光和水,不需要任何交流與思考。后來(lái),只剩下姐姐照顧英惠,姐姐成了敘事主角,敘述著英惠一步步走向新生的過(guò)程。
姐姐不能理解妹妹為什么要變成一棵樹(shù),反而認(rèn)為妹妹這樣的行為是不負(fù)責(zé)任的。但是當(dāng)姐姐真正克服了內(nèi)心對(duì)于死的恐懼,并從內(nèi)心深處感受到了世界的荒誕之后,她理解了妹妹為變成一棵樹(shù)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感受到了妹妹所受的痛苦,妹妹一句“我為什么不能死”叫醒了她。當(dāng)一個(gè)人對(duì)于這個(gè)世界已經(jīng)失望透頂,沒(méi)有任何留念之后,為什么不可以自由地選擇去死?薩特曾說(shuō):“世界是荒謬的,人生是痛苦的。”姐姐在看著妹妹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過(guò)程中也在不斷地重新審視自我,漸漸地她理解了妹妹“不是不想活下去,只是不想像我們一樣活下去”,不想像這個(gè)世界上的大部分人一樣如行尸走肉般活下去。
后來(lái)妹妹再一次面臨被強(qiáng)行喂食時(shí),姐姐做出了與上一次完全不同的舉措,這一次她選擇站出來(lái)反抗,阻止其他人為了“拯救”妹妹生命而做出的強(qiáng)迫行為。她選擇尊重妹妹的自由,與這個(gè)世界的荒謬相抗衡。當(dāng)一切塵埃落定,姐姐也獲得了新生,姐妹倆都如飛鳥(niǎo)一樣飛向了廣闊而自由的天邊。
“數(shù)不盡的樹(shù)木變成了波濤洶涌的樹(shù)海”,一場(chǎng)烈火燃燒了一切。姐姐也是一個(gè)備受壓迫的人,但是姐姐和妹妹不同,姐姐作為一個(gè)母親、家里的長(zhǎng)女、長(zhǎng)姐,她還有自己的責(zé)任,需要撫養(yǎng)兒子、照顧妹妹,有著無(wú)法擺脫的社會(huì)性,姐姐也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不斷地覺(jué)醒,不斷地領(lǐng)會(huì)到妹妹的痛苦,妹妹在軀體和靈魂上重獲了新生,而姐姐由于無(wú)法擺脫的責(zé)任只能在精神上獲得解放,姐妹二人都向讀者展示了樹(shù)火的含義——“樹(shù)是熊熊燃燒的綠色火焰”。綠色象征著生命,一棵棵樹(shù)是一位位女性,希望所有女性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意義與價(jià)值,敢于反抗暴力,勇于拒絕不合理要求,去尋求自己靈魂上真正的自由。
三毛曾說(shuō):“如果有來(lái)生,要做一棵樹(shù),站成永恒。沒(méi)有悲歡的姿勢(shì),一半在塵土里安詳,一半在風(fēng)里飛揚(yáng);一半灑落蔭涼,一半沐浴陽(yáng)光。非常沉默、非常驕傲。從不依靠、從不尋找。”樹(shù)就是這樣沉默著、生長(zhǎng)著、自由著,英惠向往著向高處生長(zhǎng),不斷地逆風(fēng)而行,去尋找靈魂的自由。愿世上所有的女性都可以直面內(nèi)心的恐懼,敢于訴說(shuō)自己的需求。敬英惠和仁惠、敬自由、敬你我!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