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2024年3月,重慶方言話劇《書月樓》在山城曲藝場首輪試演。該劇以獨特的視角講述了一個山城故事,人物鮮明,臺詞地道,展現(xiàn)了重慶方言魅力,具有濃郁地方特色。重慶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重慶市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組織青年劇評人觀摩了該劇,并進(jìn)行了專題評論。
書場茶館當(dāng)年事:《書月樓》里的重慶韻味與解放風(fēng)云
文/重慶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 陶宇
方言話劇《書月樓》借晚年重返舞臺的四川評書藝術(shù)家書齡童之口,講述了解放前夕年少的自己為求生存,來到重慶一家名為書月樓的茶館說書的經(jīng)歷,在那里他卷入了明爭暗斗中,最終書月樓迎來解放,茶館的藝人們也迎來新的生活。本劇以典型的講述人視角切入,使用跳進(jìn)跳出的手法對故事進(jìn)行引入、推進(jìn)、點評、反推和總結(jié),在全劇的起、承、轉(zhuǎn)、合中蘊含了劇作者的多重思想情感表達(dá)。
茶館和曲藝:巴渝市井風(fēng)情的再現(xiàn)
本劇的所有故事均發(fā)生在書月樓茶館,一方小天地中,各色人物悉數(shù)登場,雖為虛構(gòu),卻具有歷史的合理性。抗戰(zhàn)時期,資本、市場和人才的集聚,催生出大量的茶館,在抗戰(zhàn)勝利后生意也依然興旺,根據(jù)1947年3月《新民報》的報道記載,當(dāng)時的重慶城新舊市區(qū)共有街巷316條,而茶館竟有2659家之多,平均每條街巷有8家[1]。茶館不僅是喝茶品茗的場所,還承擔(dān)著復(fù)雜的經(jīng)濟(jì)、社會、文化等多重功能,有的面向平民百姓,有的則是以民間幫會組織、行商坐賈為主要客源。諸如書月樓這樣的茶館,往來人員魚龍混雜,易于隱蔽自身同時搜集情報,因此許多茶館早就是中共開展地下工作、進(jìn)行輿論宣傳與發(fā)展新黨員的根據(jù)地。所以,這便有了化身為書月樓掌柜、實為中共地下黨員的主角當(dāng)頭炮。通過吊腳樓式的雕塑置景體現(xiàn)茶館外部環(huán)境,簡單的二、三張木桌搭配長凳,石階上擺滿大水缸作為內(nèi)部場景,《書月樓》將這樣一家重慶老茶館搬上話劇舞臺。

主顧雖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物,書月樓卻是實打?qū)嵉牡讓影傩罩\生之地,故事的起始即為觀眾呈現(xiàn)了一幅充滿生活氣息的茶館日常:客人上座,跑堂即奉上沱茶表演茶技,隨即掌柜的干女兒月中仙便登臺演唱一段清音。因左拐子的隨從意圖調(diào)戲月中仙,她匆匆下場。隨后唱四川竹琴的二人組賈瞎子和曾聾子、金錢板二人組唐包子和張班子也先后上場表演,中間有售賣“盒兒票”(根據(jù)劇中對白,筆者猜測類似裝訂成小本發(fā)售的郵票)的小販進(jìn)場叫賣,直到年輕的書齡童闖入其間。這些民間藝人依靠茶館而生存,偶爾能收到茶客的打賞,他們之間既有抱團(tuán)又有競爭,所以面對新人書齡童的加入,他們的第一反應(yīng)是帶著些許敵意的排斥,因為擔(dān)心自己的“飯碗”受影響。而上述大多數(shù)人物的傍身之技,均是四川、重慶地區(qū)的傳統(tǒng)說唱藝術(shù),所唱、所演均表現(xiàn)出鮮明的巴渝文化色彩和濃厚的市井風(fēng)情,如月中仙的《小放風(fēng)箏》、竹琴二人組的《三英戰(zhàn)呂布》、金錢板二人組的《瞎子算命》,書齡童面對左拐子和黃昏子隨機(jī)出的《三國》考題,也展示了作為說書人的知識功底。重慶市民愛聽清音、評書、竹琴,甚至稱曲藝為“醫(yī)耳藥”,與本劇中所呈現(xiàn)的景象別無二致。

除了曲藝表演的情節(jié)安排,劇中的曲藝本身也承擔(dān)著暗示、交待故事走向的作用。例如黃昏子奉命來抓中共地下黨員時,書齡童正在講馬超追曹操。黃昏子好像聽不出其中深意,追問如何能像馬超一樣擁有“火眼金睛”,好抓共產(chǎn)黨;而書齡童話里話外卻暗指,被追得棄袍割須的曹操就好比時局下的國民黨,已是窮途末路十分狼狽。如果說選擇茶館作為故事的發(fā)生地是為了使故事更加符合史實,那么放大茶館中的曲藝元素,使其發(fā)揮交待故事背景、渲染氛圍、推進(jìn)情節(jié)的作用,則有利于將觀眾拉回真實的上世紀(jì)40年代后期,充分凸顯了那個時代重慶茶館文化的獨特性。
革命者和說書人:解放戰(zhàn)爭敘事下的失衡與缺憾
本劇以中共地下黨員與國民黨軍警之間的斗爭、與舊社會幫會組織之間的矛盾為核心,同時又呈現(xiàn)出多線交織的敘事模式:在“斗爭”這條主線之外,還有當(dāng)頭炮與花蝴蝶、書齡童與月中仙的“愛情線”,當(dāng)頭炮夫婦與女兒月中仙的“親情線”。充實這樣幾條故事線能夠豐富觀眾對主角個人生活的了解,可本劇的多線敘事也形成了幾條故事線過于均衡的觀感,原本可以占全劇更多敘事內(nèi)容的斗爭線讓位于其他線,就所占分量來說,并不明顯多過其他線,在有限的劇場時間中,就導(dǎo)致了劇情在花蝴蝶提出“以樓換人”后急轉(zhuǎn)直下,盡管在最后一場戲中,以花蝴蝶的回憶插敘了當(dāng)頭炮的犧牲過程,但對主角與反派之間斗爭過程的呈現(xiàn)卻依然令人有“不過癮”之感。這樣的均衡,不失為在敘事和人物塑造上另一種意義上的“失衡”,所導(dǎo)致的直接后果是,對本應(yīng)是劇中第一主角的當(dāng)頭炮的著墨稍顯不足。
或許出于主角戲份的偏少,又迫于展示復(fù)雜的人物關(guān)系和加速推進(jìn)情節(jié)的壓力,對當(dāng)頭炮的形象刻畫上也缺少相應(yīng)的高光點。這是本劇所描摹的一段屬于重慶人的風(fēng)云中,在人物塑造上存在的一點缺憾。作為一名長期蟄伏于茶館的共產(chǎn)黨員,當(dāng)頭炮的形象無疑是光輝的,原是一名普通說書人的他,為了解放事業(yè)偽裝成茶館掌柜,甚至不惜“拋棄”妻子、不與親生女兒相認(rèn),放棄了本該屬于他的普通人生活。但除此之外,他的面目又是模糊的,好像少了點自己的個性特點。相比之下,另外幾個主要角色的塑造反而更有層次和記憶點:一開始假裝公允的左拐子,在初次試圖侵占書月樓受挫后逐漸揭開他偽善的面孔;風(fēng)風(fēng)火火、風(fēng)情萬種的花蝴蝶為人豪爽又耿直,重感情且尤其渴望親情;年輕的書齡童知世故、會來事,關(guān)鍵時刻為了保護(hù)他人不惜以身犯險……此外,劇中提到當(dāng)初急于投身革命的當(dāng)頭炮撇下花蝴蝶獨自帶著女兒月中仙來到重慶,把女兒當(dāng)干女兒養(yǎng),又為了保護(hù)她的人身安全而對她的生活和成長多加限制,這樣缺乏相應(yīng)邏輯支撐、存在一定爭議的行為舉動,也是導(dǎo)致這個人物不夠出彩的另一點原因。

本劇故事以已入耄耋之年的書齡童的視角展開,開場畫外音提到,他是四川評書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國家級傳承人,但現(xiàn)實中并無此人。按照故事發(fā)生的年代和年輕書齡童的人生經(jīng)歷看,劇作者在構(gòu)思該人物時或許參考了真實的四川評書國家級傳承人徐勍。徐勍生于1936年,九歲喪母,10歲便浪跡街頭,迫于生計的他起初在重慶的茶館周邊提籃叫賣,在這個過程中對“說書”這件事耳濡目染,便一邊在茶館旁聽,一邊去江邊河壩開講,慢慢積累人氣,13歲得以正式拜師,開始自己的說書人生涯。這位重慶街頭成長起來的草根藝術(shù)家,也是本劇編劇袁國虎的老師。書齡童之名,以“書”為姓,又取“齡童”為名,或許是寓意劇中這位民間草根藝術(shù)家以“書”為業(yè),又有似兒童般純潔天真的心靈,把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書。
幾位曲藝人中,進(jìn)步意識最早在書齡童心中萌芽,北上“跑灘”的途中,目睹解放軍節(jié)節(jié)勝利的場景,也聽說了人民當(dāng)家作主的新理念,他將一首《解放區(qū)的天》帶進(jìn)了書月樓。當(dāng)然,此時的他對進(jìn)步思想還只是一知半解,傳播行為更多是無意識的,但從他私下教月中仙唱這首歌,到他為保護(hù)月中仙而主動站出來被當(dāng)成共產(chǎn)黨員抓走,再到結(jié)尾戰(zhàn)爭勝利他也平安歸來,整個過程中似乎沒有再對他自我覺醒、自我成長方面進(jìn)行刻畫。在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立初期,曲藝即被作為向廣大民眾特別是勞工宣傳革命思想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自新文化運動起,傳播先進(jìn)思想、堅持說新唱新也成為革命年代一些曲藝人的自覺行為,抗戰(zhàn)時期成立的“曲藝抗敵宣傳隊”便是其中代表[2]。尤其是,同為地下黨員的“盒兒票”馬前兵跟當(dāng)頭炮強(qiáng)調(diào)過,書月樓是上級交給他們的文藝陣地,那么,除了要保護(hù)書月樓不被左拐子侵吞,是否也應(yīng)該為如何改造、團(tuán)結(jié)這個陣地里的曲藝人隊伍,曲藝也反過來能為保衛(wèi)書月樓、為革命做些什么提供一些討論空間呢?本劇既以曲藝人為主角,又有曲藝元素的應(yīng)用,若能進(jìn)一步挖掘解放戰(zhàn)爭時期,重慶的曲藝在推動革命勝利的過程中發(fā)揮的獨特作用,將真實的歷史事件經(jīng)過演繹、改編服務(wù)于本劇敘事以及主要人物塑造上,想必?zé)o論是當(dāng)頭炮還是書齡童的人物成長,都會更具吸引力,作為曲藝人的覺醒,他們的故事也會給予當(dāng)代的曲藝人一份獨特的啟迪。
參考文獻(xiàn):
[1] 鐘奇,重慶茶館風(fēng)光[N].新疆日報,1949-1-27(3).
[2] 張吉宸,張小衛(wèi).澎湃歲月中的說唱音符—由電視劇《覺醒年代》中的曲藝元素想到的[J].曲藝,2022(03):24-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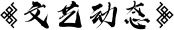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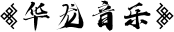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