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第五屆重慶青年戲劇演出季暨“雙城劇匯”2023成渝戲劇創(chuàng)作展演周在渝開(kāi)幕。重慶市文藝評(píng)論家協(xié)會(huì)和重慶市文化和旅游研究院聯(lián)合組織來(lái)自高校、科研院所及民間文藝社團(tuán)的評(píng)論家開(kāi)展了專(zhuān)題舞臺(tái)藝術(shù)觀(guān)評(píng)活動(dòng)。評(píng)論家們觀(guān)摩了重慶青戲季16個(gè)參賽劇目,并開(kāi)展深入研討。本系列評(píng)論文章將為讀者呈現(xiàn)本次展演活動(dòng)的精彩看點(diǎn)和藝術(shù)亮點(diǎn)。
荒誕中的希望
——評(píng)戲劇《等待戈多》
文/王靜
愛(ài)爾蘭小說(shuō)家塞繆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被譽(yù)為荒誕派戲劇的經(jīng)典之作,它的橫空出世打破了傳統(tǒng)戲劇的創(chuàng)作模式,帶來(lái)了戲劇形式的革新,被多次搬上戲劇舞臺(tái)。本次重慶青年戲劇演出季中所呈現(xiàn)出的《等待戈多》展現(xiàn)了獨(dú)特的藝術(shù)個(gè)性,試圖通過(guò)時(shí)間性中的無(wú)數(shù)瞬間與靜止、舞臺(tái)空間重復(fù)循環(huán)的無(wú)意義行為,以更加具象化、夸張化的手法向觀(guān)眾展示劇作荒誕背后的精神希望。
一、瞬間與靜止中的逃逸
時(shí)間性向來(lái)是學(xué)人研究《等待戈多》的關(guān)鍵入口,舞臺(tái)戲劇對(duì)此的呈現(xiàn)也成為觀(guān)眾所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劇名中的“等待”一詞已經(jīng)直觀(guān)顯示出劇作的時(shí)間觀(guān)念,在具體的呈現(xiàn)形式上更是通過(guò)無(wú)數(shù)個(gè)重復(fù)循環(huán)的瞬間與刻意強(qiáng)調(diào)的靜止突出人物在尋求希望的漫長(zhǎng)等待中,與時(shí)間共存時(shí)的逃逸。
《等待戈多》打破了數(shù)字化概念的時(shí)間經(jīng)驗(yàn),整體上采用許多相似瞬間的重復(fù)與靜止體現(xiàn)人物的生命體驗(yàn)。在戲劇的第一幕中,戈戈脫鞋的動(dòng)作重復(fù)了很多次,起初他坐在樹(shù)下,兩只手使勁地拽、筋疲力盡,累得不停喘氣。稍作休息后又開(kāi)始重復(fù)同樣的動(dòng)作。狄狄提出跳塔的提議后走到戈戈身邊,幫助他脫鞋,加入了這一不斷重復(fù)的瞬間。直到第一幕即將結(jié)束,波卓和幸運(yùn)兒上場(chǎng)之前,戈戈一直停留在與“鞋”有關(guān)的瞬間。觀(guān)眾的焦點(diǎn)由此聚集在“鞋”上,作者從未明確地標(biāo)明故事發(fā)生的日期與鐘點(diǎn),而是以具體動(dòng)作的重復(fù)向觀(guān)眾展示時(shí)間的流逝。時(shí)間在此種處理中喪失了標(biāo)志事件背景意義的功能,淪為了承載人物生命信息的場(chǎng)所。與重復(fù)性的動(dòng)作并行的,還有人物語(yǔ)言的反復(fù)延宕。戈戈和狄狄的交流過(guò)程即是不停地重復(fù)對(duì)方的話(huà)語(yǔ)。例如在兩幕戲劇的結(jié)尾,都出現(xiàn)了這番對(duì)話(huà)“那么,咱們走吧?”“咱們走吧。”他們交換了彼此的臺(tái)詞,不斷重復(fù)的對(duì)話(huà)使語(yǔ)言流失了意義,變得麻木機(jī)械。貝克特在談到《等待戈多》時(shí),強(qiáng)調(diào)了重復(fù)是這一戲劇的重要原則,瞬間的重復(fù)消解了時(shí)間與人物生命之間的緊密聯(lián)系,將人物的存在帶去了更加廣闊的領(lǐng)域。

與重復(fù)性的瞬間相對(duì),靜止構(gòu)成了本次戲劇時(shí)間性表達(dá)的另一重鎮(zhèn)。在本次丁乙導(dǎo)演的這版《等待戈多》中,靜止通常以“相對(duì)”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lái)。所謂的相對(duì),即是關(guān)于人物之間表現(xiàn)狀態(tài)的對(duì)比。主從順序顛倒之前的幸運(yùn)兒可以看作一個(gè)典型的靜止。他的靜止并非僅僅表現(xiàn)在臺(tái)詞稀少,而是由他所引起的一系列連鎖反應(yīng)所帶來(lái)的集體沉默。波卓為了向戈戈和狄狄炫耀自己的奴隸,要求幸運(yùn)兒展示他舞蹈和思考的能力。他舞蹈時(shí),其余三人保持仰頭看天的停滯,隨后而來(lái)的狂歡下,幸運(yùn)兒失控了,他滔滔不絕,毫無(wú)停頓的思考再次使其他人物陷入靜止。眾多重復(fù)的瞬間消解了動(dòng)作意義的光環(huán),加劇了對(duì)人物存在的嘲諷,暗含著世界虛無(wú)的危機(jī)感,而遽然出現(xiàn)的靜止卻使非理性的時(shí)間觀(guān)展現(xiàn)出與生命的關(guān)聯(lián)。“等待”是劇作的中心,也可以理解為戈戈與狄狄對(duì)于生命拯救的期待,但在時(shí)間性的重復(fù)與靜止中,這種期待喪失了積極的意義,淪為消極的逃逸。但逃逸并非意味著劇作要陷入虛無(wú),主人公對(duì)于被救贖的期待從未徹底消失。


二、無(wú)意義行為下的抗?fàn)?/strong>
戈多作為全劇的中心,他的不在場(chǎng)構(gòu)建了整個(gè)戲劇的發(fā)展過(guò)程。在沒(méi)有起始與終結(jié)的等待中,戈多的名字被一次次的提及,人物的等待行為被分解為了無(wú)數(shù)個(gè)無(wú)足輕重,無(wú)聊機(jī)械的重復(fù)性瞬間,戈多在這些瞬間中以虛假的在場(chǎng)和抽象的名字降臨,“在而不在”的狀態(tài)使戈戈和狄狄陷入沒(méi)有盡頭的等待。為了顯示自身在非理性時(shí)間中的存在,獲得戈多的救贖,他們以眾多無(wú)意義的行為來(lái)展開(kāi)與虛無(wú)的抗?fàn)帯?/p>
此處再舉上文戈戈脫鞋這一動(dòng)作,微不足道的“鞋子”在第一幕中占據(jù)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一靜態(tài)物體的存在帶來(lái)了戈戈“脫鞋”的動(dòng)作,緊接著又引發(fā)了兩位主要人物之間無(wú)邏輯的混亂對(duì)白,戲劇由此展開(kāi)。穿在戈戈腳上的“鞋”可以看作對(duì)自由的束縛,他拼盡全力、累得氣喘吁吁也要一脫再脫,由這個(gè)無(wú)意義的動(dòng)作發(fā)泄著對(duì)抗著再一次無(wú)所獲的虛無(wú)等待。對(duì)“脫鞋”這一平常動(dòng)作的放大表達(dá)使觀(guān)眾與人物的精神在某個(gè)時(shí)刻達(dá)到了共鳴,脫不下的鞋象征著人在社會(huì)中無(wú)法逃避的煩惱痛苦。最終戈戈使盡平生之力,終于脫下了那只鞋子。他拿起看了看,摸了摸,鞋子里什么也沒(méi)有,狄狄湊上前,“你就是這樣一個(gè)人,腳出了毛病,反倒責(zé)怪起鞋子”。在狄狄看來(lái),脫鞋之于戈戈是庸人自擾,而對(duì)于戈戈而言,當(dāng)他的全部精神聚焦在擺脫鞋子上時(shí),盡管疼痛了肉體,卻在無(wú)意義的反抗中收獲了精神的撫慰。對(duì)抗絕望,追尋自由正是人類(lèi)生存的母題。
戲劇中充斥著無(wú)意義的語(yǔ)言行為,眾多大量重復(fù)的對(duì)話(huà)是“遺忘”帶來(lái)的后果。“遺忘”同樣可以看作是戈戈和狄狄對(duì)抗虛無(wú)等待的反抗。戈多時(shí)隱時(shí)現(xiàn)的曖昧蹤跡使戈戈和狄狄陷入荒誕與尷尬的無(wú)終結(jié)的等待。無(wú)法消解的壓抑和焦慮讓他們不斷尋求等待中的解脫,“遺忘”是人物采取的對(duì)抗策略,將日復(fù)一日的機(jī)械行為化為每天的新鮮事,旁觀(guān)者眼中的重復(fù)于局中人而言,是全新的開(kāi)始。
粗魯?shù)膭?dòng)作與遺忘帶來(lái)的乏善可陳的對(duì)話(huà)極大淡化了劇作的情節(jié)要素,但這一處理恰恰映射出人物的生存意識(shí)和思想狀態(tài)。戈多的“在而不在”讓人物陷入內(nèi)心的混沌,但其采取無(wú)意義的行為與荒誕的命運(yùn)對(duì)抗,在虛無(wú)中虛無(wú)地殺死時(shí)間,重尋戈多的救贖帶來(lái)了戲劇最具沖擊力的爆發(fā)。
三、不確定性里確定的希望
不確定性是《等待戈多》中反復(fù)傳達(dá)出的觀(guān)念。在后現(xiàn)代主義者的描述中,不確定性被描述為含混、多元、反叛與推翻一切,它解構(gòu)著所有已存在的秩序,但就此來(lái)看,破壞了所有確定的不確定本身就是一種確定的存在。在戲劇《等待戈多》中,正是時(shí)間、場(chǎng)景、人物的不確定帶來(lái)了人物所追尋的確定的希望。
戲劇一開(kāi)場(chǎng),戈戈和狄狄如夜游神般繞場(chǎng)行進(jìn),燈光開(kāi)啟,他們展開(kāi)了無(wú)聊的對(duì)話(huà),對(duì)話(huà)中關(guān)于時(shí)間的存在沒(méi)有具體的指示,只有“明天”“今天”“昨天”的模糊概念。關(guān)于“等待”的事件中,最重要的時(shí)間卻被作為了隱而不示的信息。時(shí)間的流逝在劇中沒(méi)有認(rèn)識(shí)連貫的順序,仿佛是突兀出現(xiàn)的,例如第二幕中的波卓仿佛是在一瞬間變成了盲人。時(shí)間的變化只出現(xiàn)在無(wú)數(shù)個(gè)重復(fù)的瞬間中,由人物機(jī)械化的動(dòng)作與不斷反復(fù)的話(huà)語(yǔ)暗示著客觀(guān)物理時(shí)間的凝固,線(xiàn)性的時(shí)間秩序已經(jīng)崩潰。

從場(chǎng)景上看,人物的活動(dòng)空間局限在一條荒涼的鄉(xiāng)間道路、一個(gè)土堆和一株禿樹(shù)。但這樣簡(jiǎn)單的空間卻隱含著更多的不確定。不明確的地理位置使觀(guān)眾無(wú)法推斷人物的家鄉(xiāng)與背景,隨處可見(jiàn)的不知終點(diǎn)的道路讓人物從未知的地方來(lái),又到未知的地方去。但路的不確定又提供了一種確定的意義,即使這條路充滿(mǎn)了未知,但它仍舊成為人物唯一可走的路,不論戈多是否會(huì)從路的盡頭降臨,路在此處的唯一性是可以確定的。
時(shí)間與空間的模糊不清使人物的身份更加撲朔迷離,戈戈和狄狄兩位主要人物從戲劇的開(kāi)始到結(jié)束始終停留在光禿禿的樹(shù)下,沒(méi)有過(guò)去,沒(méi)有身份,沒(méi)有一切可推斷出的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連接。并且就這兩個(gè)人物本身而言,他們是兩個(gè)獨(dú)立的個(gè)體還是一個(gè)已經(jīng)在等待中分裂出第二人格的患者?這一問(wèn)題同樣是難以確定的。戈戈和狄狄在戲劇中展現(xiàn)出了類(lèi)似于一人的雙面。狄狄比起舞蹈更愛(ài)思考,經(jīng)常喋喋不休,戈戈嗜吃又嗜睡。當(dāng)他們討論《圣經(jīng)》時(shí),狄狄思考的是兩個(gè)賊的得救,戈戈只記得有彩色的地圖。他們兩個(gè)似乎對(duì)應(yīng)著靈與肉的雙面。戲劇第二幕中二人的假裝謾罵和對(duì)抗,更像是一個(gè)肉體在竭力馴化雙重人格。

戲劇中無(wú)處不在的不確定好像驗(yàn)證了世界的荒誕虛無(wú)與追尋等待的無(wú)意義。但除去表象,深入剖析,卻能預(yù)見(jiàn)重重不確定下的確定性存在。時(shí)間的不確定讓人物喪失了追溯過(guò)去的記憶和能力,卻指向絕對(duì)確定的未來(lái);不確定的鄉(xiāng)村小道是未知的也是唯一的;無(wú)法分割的兩位人物卻持有同一個(gè)目的——等待戈多。等待是戈戈與狄狄賦予自身存在意義的表現(xiàn),戈多是他們對(duì)于精神世界的荒蕪開(kāi)出療愈的最后藥方,是他們用來(lái)對(duì)抗荒誕世界的武器,盡管這個(gè)武器看起來(lái)更加荒誕不經(jīng),但卻實(shí)實(shí)在在地顯示了他們與虛無(wú)對(duì)抗的勇氣與堅(jiān)持。

本次重慶青年戲劇演出季所上演的《等待戈多》,以極簡(jiǎn)風(fēng)格的舞臺(tái)呈現(xiàn)出了多棱鏡一般的戲劇效果。恰到好處的燈光變換、貼合情景的背景音樂(lè)與青年演員純熟的演技為觀(guān)眾提供了一場(chǎng)絕佳的視聽(tīng)盛宴,也傳達(dá)出人物超越荒誕,追尋希望的堅(jiān)持。戈戈與狄狄身處荒誕之中,或者說(shuō)他們本身構(gòu)成了荒誕的一部分,但仍以等待的行為來(lái)印證自身生存的意義,以無(wú)意義來(lái)對(duì)抗虛無(wú),奮力超越荒誕,尋求自我的救贖。戲劇的結(jié)局是無(wú)終結(jié)的,但正像舞臺(tái)上禿樹(shù)的幾片綠葉,無(wú)盡的荒誕中始終存在確定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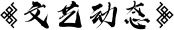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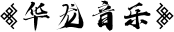
600bd524-6a81-498b-8e10-6aff1cc18895.jpeg)
